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桐 花(外一篇) 李晓文
桐 花(外一篇)
李晓文
桐 花

桐花家住草冲,是跛子润生的女儿。润生是那里的特困户,他家原有几间土房,不久前被山洪冲垮了,一家三口可怜兮兮地挤在两间临时搭起的破茅棚里。我们去那里进行对口扶贫,任务是帮他家建一栋土坯房。
那一天我们去润生家,正是绿肥红瘦的季节,山野一片清翠。临近润生家时,远远地见对面山坡上有一姑娘在挥镰割草,她一边割一边哼一些不知名的乡间小调,音韵格外凄凉,听上去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待我们走近了,那歌声又猛然收住,就像树上的鸣蝉,唱得正起劲时突然发现险情,马上屏声静气起来。
我们很快知道那姑娘名叫桐花。当我们沾满泥巴的双脚刚刚靠近润生家门坎,那跛子便立即转过身去扯开破嗓朝山上呼唤:桐花,桐花,家里来客人了,还不给我到代销点打酒去!便听到对面山头哎了一声,很快就有一株天籁向我们走近。桐花悄悄地放下竹篮,又悄悄地提了酒壶出去,我们意欲制止,眼前己没了她的踪影。跛子满脸堆笑,将我们迎进他的茅棚,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他大约早就知道我们的来意。棚子里阴暗潮湿,有一股浓浓的霉味直往我们鼻孔里钻。桐花娘躺在床上,脸色腊黄,看样子病得不轻。家中陈设简陋,除一床一桌和几件残肢断腿的家具外,别无长物。我的心里有些发紧,便装作察看灾情的样子往屋外走,却正巧碰上桐花打了满满一壶酒回来,额头上冒着细密的汗滴,脸有些微红,嘴里喘着粗气。
她低低地叫了我一声叔,我努力摆出和蔼的样子说桐花你坐啊,她便拘谨地坐在我对面前 的门坎上,且默默无语,只静静地睁了一双明眸看我们,就像一朵带露的山花无语地开在一株卑微的杂木上,让我无端地生出几分怜爱来。棚子里气氛沉闷,大家心照不宣地扯些不咸不淡的话题,末了,同来的小张说,李领导,你把我们这次来的目的讲讲吧。我于是说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考察灾情,根据乡里的意见,决意为润生家建一栋土坯房。润生先是满脸惊愕,继而又现出满脸的惊喜来裂开嘴偷偷地乐,两个大板牙毫无保留地露了出来。我悄悄地问桐花你读书没有?成绩如何?回答是读过,又停了,家里没钱,供不起。那声音就越发有如蚊吟般细小了,好像有说不尽的怨艾和委屈,不知道要如何排解。这世界真是邪乎,能读书的没钱读,不会读的却可以用钱买文凭,买一生的衣食奉禄,而天下众多的桐花们却注定只能像山野的花草一样自枯自荣,寂寞无主。
跛子润生还真能干, 一会儿功夫便弄出几样小菜来,香喷喷的直吊我们的胃口。润生一边忙不迭地给我们挟菜,一边热情地敬酒。那菜虽不及城里的名贵,却是地道的山货,有荠菜、笋丝、神仙菜(一种野菜),虽然经了一冬的浸泡,吃起来犹觉清香满口,只是那酒的味道却苦了点,有一股浓酽的红苕味。便想,这也许就是山里人的生活本色吧,只是润生家一年怕是难得有几餐这样的丰盛,我们这一桌下去,不知要吃掉他家几天的口粮呢!饭毕,我们均自怀中掏钱,跛子说啥也不要,说政府老远来看我们,吃点山野土菜,不成敬意,岂能再收钱!我们说这钱你无论如何得收下,这是我们公家人的规矩,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便不好意思地收了,满脸愧色,倒好像是他欠下我们许多情。这期间,桐花手脚麻利地收拾起桌上的一切,并不说话,可我却分明从她那一对水灵灵的眼睛里读到了什么。酒足饭饱后,我提出为他们一家到茅棚前照像,桐花娘说啥也不参与,桐花羞羞地想照又不好意思,且不知摆什么姿式好,倒是跛子润生乐哈哈地一点也不谦让,他大约看出了这玩意儿弄出来会给他带来什么好的运道。
终于要走了,桐花说,你们就走啊。我们说要回去汇报呢。桐花又说还来吗?我们又说,还来,我们还要给你家建房呢。此时,太阳己经偏西,温暖的阳光照着山野里的一切,呈现出无限生机。
一个月后,润生家的土坯房盖起来了,我们又去了一趟草冲。临别时,我问桐花,想不想到城里去打工?桐花先是一喜,继而又默然,只听她轻声说,家里离不开我哩!没想到短短一月不见,桐花比先前又沉重了许多,那些本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天真和烂漫在她身上己断然无存。也许是生活本身赋予了她太多的重压?也许,她将一生一世呆在这大山里了?
遥望着那片蓝色的山地,我在心底默默为她祝福。

草 儿
像一只粉红的蝶儿翩然于无边的空寂,草儿在地里割麦。四野无人,只有风刮过麦浪的声音。阳光沉沉地压着麦杆,让它们不堪重负地低下了羞涩的头。太阳毒着呢,眨眼间工夫,便让小麦们都抱上了金娃娃。太阳是男人吧?他能让世上所有的母性都圆一个温馨的梦!草儿这样想着,汗水就潸潸地流下来了,粉红色的衣裳有些湿润,而且讨厌地沾住了身子,让日渐丰满的心事恰到好处地鼓胀起来。耀眼的阳光下,能隐隐地看到一道洁白的遐想。
为什么只让我们的草儿一人割麦?其他人都干啥去了?十八岁的草儿说:没法子呐!母亲在家带弟妹、养牲口,不得空,父亲清早就去山外赶集了,说是要抱回一条猪仔哩。猪仔好,草儿喜欢猪仔,最好是母的,长大了能生许多白白胖胖的小猪仔,一窝猪仔能卖千多元哩!那样,弟妹们读书就不用愁了,父亲的酒壶也不用难为情地背靠墙壁,母亲也该换一件新褂子了;至于草儿嘛,最好是能买些女孩子的小物件——上次听打工回来的小梅说,山外的女人“做好事”都用卫生巾呢,那东西又软和又舒适,谁像咱,一块红红的粗布,缠着一迭厚厚的草纸,又脏又累,夹着多难受!
太阳缓缓地升上天去,草儿有些渴,也有些饿,便走到坡下的小溪边咕噜咕噜喝了一通山泉水,就觉得那水透心的甜,比吃西瓜还好。想起城里人掏钱买水喝的样,草儿就想笑:那种水有啥好喝的啊?怕还比不上咱家山塘的水来得滋润呢!便想,要是能将城市搬到山上来就好了,这满沟的水就不会白白的浪费掉了。草儿灌足了水,又用竹筒打了满满一筒带上坡去,然后在麦地边的一棵松树下坐了,狼吞虎咽地啃起了干饭。一只蚂蚁悄没声息地钻入她的衣襟,选肉厚处狠狠地蜇了一口;草儿立即痛得跳将起来,忙伸手抓住那可怜的倒霉虫,恨恨地说,我辛辛苦苦干了半天活还吃不到半点肉,你偷偷摸摸跑上来就想吃现成啊?呸!便用力将蚂蚁捏碎了。不知为什么,小蚂蚁的入侵将草儿的心绪搅成了一堆乱麻,她不由地想起那些在山外打工的姐妹来了,她们在干什么呢?是上街逛商店?还是进公园拍照片?抑或跟城里人谈恋爱?乡下人跟城里人恋爱己经不算稀奇了,据说山里边的阿珍找了个广东佬,还寄了好多钱回来,她家都修上红砖楼了!阿珍是草儿的远亲,模样儿虽然长得俊,但若与我们的草儿相比,就显出距离了!草儿不由地站起身来,欣赏着自己优美的身段,心想,我要是能出去,怕也能像阿珍一样找个城里阿哥吧?便怨父亲当初不该阻挡她出去,要是春节后跟姐妹们一块儿走了,说不定现在也寄回了大把大把的钱,那样,家中的日子就有了活水,自己也不至一个人孤零零地到山上来受小蚂蚁的气了,说不定正与某城里阿哥在公园的长椅上谈爱哩!.......草儿这样想着,不由得痴痴笑了,脸上就飘起两朵好看的红霞来。
草儿一边奋力割麦,一边想象着自己也被时间一寸一寸地割倒,心里就有些害怕,就有了几分不甘。不是吗?草儿的父辈们不都是这样一茬又一茬地被命运所宰割吗?草儿想起母亲,心里就隐隐地有些作痛。原来水灵如柳枝一样葱茏的母亲啊,转眼间变得跟墙角的水桶一样臃肿了!母亲每天像牛一样辛勤劳作,可苦难仍然像影子一样尾随着她。难道等待自己的将是同样的命运吗?前几天,山那边走来一个说媒的,不知跟父亲嘀咕些什么,那老乌鸦的嘴里怕是唱不出好调来的,我可得小心了。明年,草儿心里恨恨地想,明年我是决计要走出这片大山的了!
太阳己没了先前的火辣,好像显得有些温柔了,但对于 草儿烦恼的心绪己没有半点抚慰。草儿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奋力收割麦子,无论如何,今天这块麦是一定要割完的,否则,等雨季一来,不但红薯插不上,麦子怕也要烂在地里了!谁知这样一激棱,草儿就觉得有些尿急。山里自然没有茅厕,没有那种立体的现代文明,但山野中也相对缺少我们嘴中的风流韵事。草儿看看四周无人,便大胆地蹲在了麦地上。这时,一只鸟儿锐叫一声冲上天去,吓得草儿慌乱地提起裤子,嘴里连连骂道:杀千刀的叫天子,你家死人啦?也来欺侮咱!……
时间在不慌不忙地流逝。太阳落山的时候,草儿终于收割倒了最后一株麦子。她直起身来,面对着群山长长地了口气。那圆圆的杏眼顾盼着远去的夕阳,心儿早已飞到很远的山外去了。
夜幕刷的一声落了下来,横在草儿面前的又将是一个疲惫的孤夜。
李晓文,男,湖南新化人。作家,书画家,美术评论家。现居广东江门。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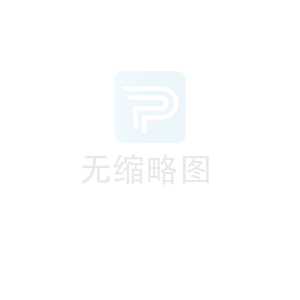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