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五台山:烟火梵音间,照见自渡
作者 南佳利
晨雾漫过商洛山坳时,后视镜里的秦岭的轮廓逶迤成水墨长卷。我与老公从商州老家出发,女儿则从北京奔赴忻州,这场跨越三省的汇合,始于女儿那句“五台山的香火能照见人心”。她研究品牌营销,连旅行攻略都做得像商业策划案,打印出来的A4纸上,标注着景区公交时刻表、庙宇开放时间。老公也把供品清单都列得清清楚楚——供果要新鲜的,香要买佛点头牌的,香油需是古法压榨的……女儿看到这些,她笑着说“这是对信仰的仪式感,就像品牌要传递诚意。”
车窗外的景象渐渐从秦岭的浓绿转为晋地的苍茫。途经渭北高原时,干涸的河床像大地皲裂的伤口,两岸的秋苗蔫头耷脑地伏在田垄上,叶子卷成焦边的纸卷。果园里的苹果倒是红得诱人,却挂在枝头透着一股缺水的紧绷感。我隔着玻璃望着远处龟裂的土地,入夏以来,北方的旱情早已在新闻里刷屏,此刻亲眼所见,才惊觉那“速降甘霜”的祈愿,并非空泛的祷词。

在从忻州去五台山的大巴车上,“妈,你看那片云。”女儿指着车窗外。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在山梁上,却迟迟不肯落下雨滴。我心里默祷:若真有菩萨显灵,先解这人间旱情吧。这念头一起,忽然觉得此行的意义超越了寻常旅行——不是打卡山水,而是带着众生的苦乐,去叩问一座山的慈悲。
三个小时的车程里,我透过车窗左看右眺,山形逐渐变幻:不再是秦岭的险峻孤峰,而是连绵起伏的缓坡,像被巨手揉皱的绿绸。车入景区时,满目的苍翠几乎要溢进车窗——针叶林与阔叶林交错生长,深绿、浅绿、墨绿层层叠叠,铺成厚得能陷进去的绒毯。最妙的是那些庙宇,红墙黄瓦在绿意中忽隐忽现,檐角的铜铃被山风拂动,叮咚声顺着山谷流淌,与车载广播里的诵经声混在一起,竟有种奇妙的和谐。

景区八路公交车是免费乘坐的,每到一处景点便自动停靠。女儿忙着拍照,镜头里既有飞檐斗拱的细节,也有远处山峦的全景,“你看这色彩搭配,”她指着取景框,“红黄蓝绿,都是饱和度极高的原色,却一点不艳俗,这才是顶级的视觉营销。”
女儿订的酒店在台怀镇中心,推开窗就能看见大白塔的鎏金塔刹。放下行李时已近正午,街边的素斋馆飘来炒蘑菇的香气。我们随便吃了自带的面包,喝了点油茶,便直奔五爷庙——主供五爷(文殊菩萨化身),以灵验著称,求财、求事业者络绎不绝。素有“到五台山不拜五爷,等于白来”之说。可庙前的景象让我震惊:钢管搭建的廊道里,人群像被压缩的沙丁鱼,前后摩肩接踵,半步挪动都需耗费几分钟。七月的暑气蒸腾着汗味与香火味,一位拄拐杖的老太太被家人搀扶着,每向前挪一步都要默念一句“五爷保佑”。

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挤到殿门前。院内更似沸腾的锅,香灰在烈日下扬起呛人的烟尘。我捧着从家带来的供品,在拥挤的人潮中勉强转身,看见女儿正举着手机录视频,镜头里是无数双合十的手,有的粗糙布满老茧,有的纤细涂着指甲油,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你说这么多人,五爷能顾得过来吗?”我凑近她耳边喊。她关掉录像,认真道:“或许不是五爷在顾,是人心在互相照见。”拜过五爷,我们又去附近的广化寺,罗睺寺,塔院寺,显通寺,菩萨顶,普寿寺……,直到暮色里的庙宇褪了红,染了金,檐角铜铃在晚风中轻响,像无数祈愿在回落。19点才回到酒店。

第二天,计划登黛螺顶。清晨,台怀镇还笼罩在薄雾里,我们就出发了,边走老公给我和女儿科普相关黛螺顶的知识——因山势如螺、松柏青翠得名,登顶需攀登1080级台阶,素有“小朝台”之称——这里供奉五方文殊,可一次性朝拜五座台顶的文殊菩萨化身……说着就来到黛螺顶山脚下,这里早已聚满了人,卖香烛的小贩用晋语吆喝着,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登顶有三条路:一条是绕山的水泥路,一条是1080级的石阶,标着“大智路”,暗合佛教“消除108种烦恼”的说法。还有可以坐索道(几乎没人选)。我们决定走石阶。我望着那些正在跪拜的身影——有年轻情侣三步一叩,额头碰在冰凉的石头上,发出“咚”的轻响;有母亲背着孩子,每爬十级便停下来喘息;最让我心惊的是一位白发老者,穿着褪色的蓝布褂,双手戴着护膝,膝盖落地时,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他每拜一次,都要把额头贴在台阶上,像在亲吻大地。

我跟着人流向上,前二百级台阶还算轻松,到第三百级时,膝盖开始发酸。停下来喝水时,看见刚才那位老者已超过我们,他的护膝磨出了毛边,额头前的头发被汗水粘成一绺,却依然固执地重复着“跪-拜-起”的动作。“他求什么呢?”我问老公。他望着远处的云层,缓缓道:“或许什么都求,或许什么都不求,只是在还愿。”
爬到第六百级时,我累得靠在水泥扶拦上。向下望,人群像一条蜿蜒的长蛇,向上看,石阶消失在云雾里。忽然想起路上看见的旱田,想起那些蔫黄的秋苗——我们求雨,求丰收,求安康……可这世间的苦难,哪是一炷香就能化解的?恰在此时,一位背着帆布包的姑娘从我身边经过,包上绣着“山西农大”的字样,她蹲身抚过叶脉,笔记本上字迹工整:“华北落叶松,旱季存活率73%(2024年同期89%)”。见我打量,她笑答:“做植被调研呢——五台山生态像易碎的琉璃,游客多了,草木也会‘累’出病来。” 指尖划过叶片的弧度,藏着护林人的温柔。

这瞬间,我忽有所悟:原来虔诚不止于跪拜,更在于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双手守护众生。当我终于踩着最后一级台阶登顶时,汗水已浸透了衣衫,膝盖也又酸又痛,却在望见云海的刹那忘了疼痛。天蓝得像倒扣的琉璃碗,云团在山尖流动,远处的东台、南台、西台若隐若现,山风带着松涛扑进怀里,每一口呼吸都裹着负氧离子的清甜。

五方菩萨殿里,香火浓得化不开。女儿往功德箱里放了钱,又仔细添了灯油,火苗“噼啪”一声窜高,映亮了她专注的侧脸。我跪在蒲团上,望着殿内林立的菩萨像——文殊菩萨手持智慧剑,面目慈悲却又透着威严,忽然想起排队时听见的对话:有人求赌运,有人求仕途,有人求姻缘,甚至有人对着菩萨抱怨“求了三年都没灵验”。唉!“菩萨也不容易啊。”
走出大殿时,我忍不住对女儿感慨,“众生欲念万千,善的恶的,都求菩萨保佑,该怎么‘普渡’?”我又记起遇见的农大姑娘,她做调研,是不是比跪在庙里求雨更实在?”

突然像有道光劈开混沌。是啊,我们总把“保佑”理解为不劳而获的捷径,却忘了菩萨真正的“渡”,是教会人自渡。就像那干旱的土地,若无人引水灌溉、改良土壤,即便天降甘霖,也难改荒芜;就像人生的愿望,若不付诸行动、踏实耕耘,即便拜遍菩萨,也只是镜花水月。
下山时我们走的是盘山路,遇见几个背着行囊的徒步者,他们要花三天时间完成77公里的大朝台。“为什么不坐车?”我问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抹了把汗,指着远处的山坳:“你看那片松林,去年还是光秃秃的,今年就长出新枝了——有些路,必须自己走,才能看见变化。”
这话让我想起登黛螺顶时的顿悟:1080级台阶,难的不是攀登,而是在疲惫时依然相信“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则必成”;朝拜的意义,不是向菩萨索取,而是在跪拜中学会敬畏与谦卑。当我们在五爷庙前排队两小时、膝盖跪拜到发青时,收获的不是愿望的捷径,而是对“坚持”的体认;当我们看见八旬老者三步一叩首时,懂得的不是迷信的狂热,而是信仰对人心的淬炼。

离开五台山那天傍晚,天空终于飘起了细雨。车窗外的秋苗在雨中舒展叶片,果园里的苹果被雨水洗得发亮。女儿在攻略本上勾勒思维导图,笑言:“五台山的品牌逻辑太妙——自然与佛韵交融,每处景致都是触点,连香火的余韵都成了记忆锚点。”
我望着雨雾中的山峦,忽然明白:五台山的智慧,不在庙宇的宏伟,而在它让每个来者都能照见自己——虔诚者看见信仰,疲惫者获得宁静,思考者懂得取舍。就像那些在旱地里依然扎根的秋苗,人活一世,重要的不是祈求菩萨赐予顺风,而是在风雨中守住本心,用双手耕织属于自己的“天时地利人和”。
三天后,女儿返京,我们回到商州。如今翻手机里的照片,黛螺顶的云海、五爷庙的人潮、农大姑娘的笔记本,让我感悟到:这场旅行,不止是膝盖的青痕和登顶的喜悦,更是懂得了“所求皆所愿”的真意——只要心怀善念、努力前行,命运自会在转角铺路。菩萨的“普渡”,从来藏在众生的汗水里,藏在每一步踏实的“自渡”里。
值班总编辑 贺文生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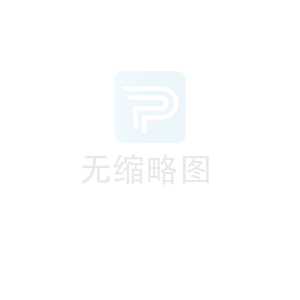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