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感恩
作者:曹安贵
一
小学毕业,因时代和家庭历史背景的原因,便无书可读。于是,12岁的我便成了放牛娃,这是我的第一个“职业”。每日挣得两分的劳动工分。对于一个小小少年来说,放牛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无论晴天、雨天、热天、寒冬、下雪都得拉着牛出去放牧。若是农忙时节,还得割青草背到田间地头去喂牛。雨水靠天,耕地靠牛。在山区农村,耕牛是每家每户重要的生产工具,一定要饲养好。否则,吃饭就成了大问题。
放牛这活倒也不难,也说不上苦。最苦的是农忙时的割草和秋收后的收谷草。割草就要早起上山,天空微微露白,晶莹剔透的露水沾满了绿油油的青草,这时候的青草是最好的,又嫩又有露水,容易消化。但割草人就会湿透一身的衣、裤、鞋子。湿透的衣裤、鞋子往往靠自身体温用整天的时间才能捂干。割草是一定会受伤的,很多青草的边缘带有锯齿,稍不留神,就会划破手指。再则,左手食指被镰刀连续地割伤指骨,致使指关节严重变形。如今,被镰刀割伤的印痕伴随我一生,这是我的成长记忆。
收谷草要抓住晴朗的天色,天公从不打招呼,它比较任性,说不准那时就下雨。晒干的谷草要抢时间运回来置放于通风、干燥处储藏,给牛备足过冬的草料。为了抢时间,每次多我就多背些草,往往是不堪重负,被成捆的谷草压住,跌倒,再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有时候,累得喘不过气来,依然要坚持。一定要挺住,因为我是男子汉,不能被村里的同龄人小瞧,我们都在暗暗地比拼。哪怕是筋疲力尽,也只能靠自己,不断挑战自己的负重潜力。荒间野外无人帮助,全靠自己的耐性和蛮力支撑着。
天长日久,稚嫩的、柔弱的身体经受不了风寒湿热的长期侵袭,两年后的一天早上,发现右脚趾的食趾关节红肿、疼痛。中午去公社医院买了些伤湿止痛膏之类的药贴上。在那个年代这种小病算不了什么事,也没太在意,照常放牛。
一个星期过去了病没有好转,反而日渐加重,放牛的同伴说:“可能是瘅,回去叫我家婆给你扯瘅药来包。”谁知这个病,像个发疯的魔鬼,缠绕着我并逐步露出它的狰狞面孔,而不肯离去,大有夺命之势。右脚食趾关节痛后,母趾关节痛,依次其它各个趾关节;踝关节、膝关节、右下肢各个关节先后疼痛。左下肢各个关节也紧跟其后。下肢痛完痛上肢,紧接着脊柱也开始疼痛,最后停留在颈部右侧的第二、第三刺突之间不动了,形成结节,致使颈部僵硬。
二

这一病程历时一年,对于一位少年来说是多么的不幸。如果苦难注定要伴随着我的成长,就一定与时代背景下的家庭相关,从形式偶然中就存在因果相关的必然。也会成为我成长过程中的幸事,从苦难中去体悟人生,可能获得某种特殊经历下的特殊价值。感悟生命的意义,认识生命的韧性。但眼前的一切现实,对于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却是无能为力。对于受尽欺凌的贫穷家庭,母亲又能怎么办呢?除了让我去公社医院打几支“链霉素”,开上些“安乃近”或“阿斯匹林”对付着,之后就只能听天由命。
我时时看到母亲偷偷地为我流泪,自责的心情流露于只言片语间,发现了我的存在便欲言又止,只有那一声声凄楚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向我诉说母亲内心中情感交织,千般无奈的思绪……
面对街邻,长辈们对我投以可怜、同情的眼神,并窃窃私语:“小小年纪,得此怪病,真是天作孽呀。”初听到这样的话语和同情的目光,会让我的情绪翻江倒海似,泪水如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听多了就会麻木,无所谓。就像邻家大叔说我的那样:“这娃儿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讨债鬼。”我有时自问:“我是个讨债鬼吗?我真是一个讨债鬼吗!”我无法回答,仿佛在是与非之间。是!我又向谁讨债呢?无疑是我的父母。而我的父亲像个“影子”般的存在,好像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
难道母亲就是我的债主了?因为我的“追讨”,已经让母亲心力交瘁,筋疲力尽了。我不仅榨干了母亲的乳汁,同时正在榨取母亲的精气神,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吸的气息越来越短促低沉。土家族那固有的倔强目光也越来越呆滞散淡。谁是真正的欠债者在我的心里自问?毫不含糊:“就是我!”真正欠债者不是母亲,而正是“我”的思绪向我袭来,汇集为强大的心理风暴击打着我的“良心”,叫我痛不欲生。这一刻我宁可以一死向母亲请罪。深重的负罪感使我拿起了尖刀对准我的心口……
然后刀并没有刺进去,不是我贪生怕死,也不是母爱的召唤或对兄姐情感的牵挂,而是“我还没有活够”的自我意识在心里的倔强呐喊。
三
病情越来越严重,已呈现左侧身体麻木,脚无力,常跌跟斗。手无力,端不住碗。其状已是半身瘫痪。这年的十月过后,母亲把喂的唯一的一头百十斤重的猪卖了,叫我哥(当年18岁)带我去遵义大医院看病。
乘车颠簸了几个小时到了遵义,看病首选是大连医院学。第二天挂号,排队候诊,最后得到一句:“你们到专区医院去看,我们没有这套设备”。于是,隔天我哥又带我去专区医院,同样的挂号、排队候诊,也得到了医生同样的拒绝之词:“你们到其它医院去看吧,我们无能为力。”于是我跟哥哥说:“不看了,回家吧!”
本地区两家权威的医院都无能为力,这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事情。这对于我哥和母亲的想法就多了许多复杂和纠结。而对我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和纠结的思绪,相反却多了一份坦然,因为我第一次进了“大城市”,也算初见“世面”。大城市并没有特殊的记忆让我回忆,也就是大城市而已。就连两大医院推诿的医生也没有引起我情绪的波动。仅此就够了,成全了我第一次无奈,却有纪念意义的远行。
回到家,依旧坐在我家街檐上的一把破椅子里,等待病魔对我最终的判决。看着偶尔驶过的一辆载重货车,隆隆的轰鸣声卷起阵阵的尘浪向街的两边扑来,让行人避让不及。跟在农民身后很不情愿去“上工”的老牛,将头奋劲的昂起,不管农民怎样用力的拉扯,老牛仍然踌躇不前,似乎是不愿与我告别…… 匆忙的行人一批又一批地走过,他们似乎并不关注我还存在。我的心理活动证明我还存在。人人都忙,唯我独闲。这种自慰自欺的思绪,让我内心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这一思绪一滑而过,另一种思绪又冒出来,人人有用,而我无用,我就是一个“废人”的悲哀情绪让我整日无语,目光呆滞。
四
一天,关松大哥从我坐的街檐路过,他是大队新选的“赤脚医生”,其特长是中草医,全凭他的勤奋和对中草医的悟性而得到乡人的认可。他问我:“兄弟,还没有好哇?”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我用极低沉的话语回答他。他又问:“好几年了吧?”我回答:“三四年了。”他接着问了生病的起因,发展过程及各个阶段病情表现的症状。我一一作答。他略思良久,紧锁的眉头舒展开,面带笑意但挺严肃地对我说:“兄弟,你这个病为什么没人能治,主要是病因不明,叫什么病也无从得知。我若用草药帮你治,只能是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你如何想?”毛毛哥(关松小名)你帮我治病,真感激不尽。我已经是个“废人”,那里还是活马,你就当是匹死马来治吧。
无论结果如何,情意都大如山;我都不会忘记。关松哥听了我的回答连声说:“行,行,行,叫你家哥下午来我家拿药。”
下午我哥去关松大哥家取了两付水药,一付酒药回来,并告诉我:“药煎好后开始要少吃,逐渐加量,如果痒用木棍刨,不要用手抓。”我连声说,好,便迫不急待去煎药。睡前我喝了一大碗又苦又涩的药汤。
真是“良药苦涩利治病……”半夜醒来,一身奇痒。点上煤油灯看,周身通红,遍布指甲大小的疙瘩。两天后皮肤不红了,疙瘩渐散了,人自感神清气爽了,手脚麻木感没那么严重了。两付水药吃完,其病状减退一半。于是去关松哥家跟进两付水药。月余病状全部消失,我痊愈啦!
五
从生病之时算起至痊愈,整整四年半。我经历了与我年龄不相匹配的特殊经历,无情的病魔对我身心的摧残,已被视为无药可治的“废人”。母亲不言放弃,哪怕是苟延残喘的苟活也行,就会有希望。对于一位重病患者,生理上的折磨是一方面,因病而带来心理上的刺激和折磨可能会成为患者生理,心理崩溃的潜在因素。我之所以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一是母爱的不言放弃,二是我当时只是未曾涉世的少年,对生死没有过多或深入思考的能力。简单的听天由命,就是一种坦然,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
我是一位不幸者,有权指责上天对我的不公。又是一位幸运者,关松大哥施以有缘之药,让我体验了“药到病除”的神奇效果。救活了我这有缘之人。我当以真情回报,思之,关松大哥给予我的是情吗?若以情相待,就显出我的浅薄。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满腔的真情,其它一无所有,分文未取是拯救者的无私医德。那是恩!是拯救,再造生命之恩。
恩者一曰父母的生养之恩。是无私的给予,谓之为“恩受”。二曰生命的拯救之恩。前者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后者为救命的恩人。所以认为“恩”是至高无尚的给予,具有相应的神圣性,任何俗情的应对,都是对至高无尚的亵渎。我把父母的恩受之恩,关松大哥的拯救,再造生命之恩时刻铭记于心。为什么说:“大恩不言谢!” 任何形式的情感表达都是渺小的,恩则是无比伟大无私的给予。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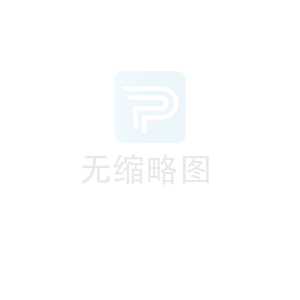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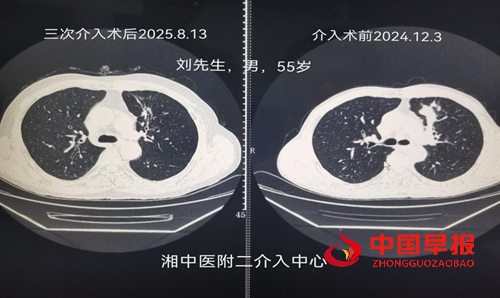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