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莫言作品的外译本,结尾改成了原作相反的结局
众所周知,莫言获得国际文学界的大奖——诺贝尔文学奖,与其翻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其背后的翻译问题,大家(包括国内的翻译界)并不都清楚。日前读到的一位老翻译家在莫言获奖后说的一番话即为一例:他对着记者大谈“百分之百的忠实才是翻译主流”,要“逐字逐句”地翻译等似是而非的话,
却不知莫言作品的外译与他所谈的“忠实”说相去甚远——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恰恰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译,而是“连译带改”地翻译。他在翻译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然而事实表明,葛浩文的翻译是成功的,特别是在推介莫言的作品并让其在译入语国家切实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方面。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指出,德译者甚至未根据莫言的中文原作,而选择根据其作品的英译本进行翻译,这说明英译本迎合了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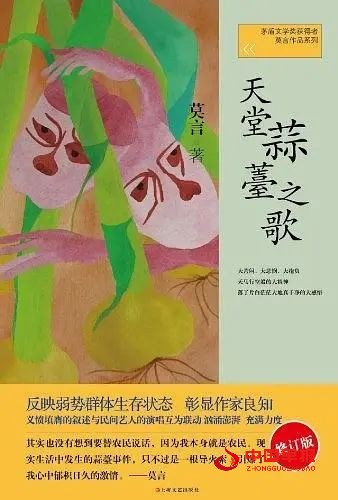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
严格而言,对莫言获奖背后的翻译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传统翻译研究中仅仅关注“逐字译还是逐意译”的狭隘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而进入了译介学层面,即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其实,经过中外翻译界一两千年的讨论,前一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翻译应该忠实原作”已是译界的基本常识,毋需赘言;至于应该“逐字译”“逐意译”,还是两相结合等,有独特追求的翻译家自有其主张,也不必强求一律。倒是后一个问题,即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甚至无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外来的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学作品一直有强烈的需求,所以我们的翻译家只需关心如何把原作翻译好,而甚少甚至根本无须关心译作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外译问题。在国外,尤其在西方,尚未形成像我们国家这样对外来文化、文学有强烈需求的接受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培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受众和接受环境的问题。
归纳起来,莫言获奖背后的翻译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
首先是“谁来译”的问题。 莫言作品的外译者,除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还有法译者杜特莱(Noël Dutrait)夫妇和尚德兰(ChantalChen-Andro),瑞典语译者陈安娜等。这都是些外国译者,他们对莫言作品在国外的有效传播与接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诺奖评委马悦然(GöranMalmqvist)所指出的,他们“通晓自己的母语,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现在(中国国内的)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这个糟糕极了。翻得不好,就把小说给‘谋杀’了”。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年6月6日—2019年10月17日 [1] ),瑞典人,著名汉学家、瑞典汉学研究者、翻译家。曾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static/upload/image/20200820/1597925898280629.jpg)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年6月6日—2019年10月17日 [1] ),瑞典人,著名汉学家、瑞典汉学研究者、翻译家。曾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的说法也许不无偏激之处,因为单就外语水平而言,国内并不缺乏与这些外国翻译家水平相当的翻译家。但是,在对译入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位等方面的把握上,我们还是得承认,国外翻译家有着国内翻译家较难企及的优势。这是我们在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时必须面对并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次是作者对译者的态度问题。 莫言在对待他的作品的外译者方面表现得特别宽容和大度,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他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奴隶”,而且表示明确放手:“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正是由于莫言对待译者的这种宽容大度,他的译者才得以放开手脚,大胆地“连删带改”,从而让莫言的外译本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差异”的“隐形门槛”,成功地进入了西方的主流阅读语境。有人曾对莫言作品外译的这种“连译带改”的译法颇有微词,质疑说:“那还是莫言的作品吗?”对此,我想提一下林纾的翻译。对于林译作品是外国文学作品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人表示怀疑吧?这里其实牵涉一个民族接受外来文化、文学的规律:它需要一个接受过程。我们不要忘了,中国读者从读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到读今天的《大卫·科波菲尔》乃至《狄更斯全集》,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的读者对东方包括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真正的兴趣,却是最近几十年才刚刚开始的,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就会对全译本,以及作家的全集感兴趣。但是,随着莫言获得诺奖,我相信,在西方国家很快会有出版社推出莫言作品的全译本,甚至莫言作品的全集。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曾古文翻译《茶花女》与《迦因小传》。
再次是译本由谁出版的问题。 莫言作品的外译本都是由国外的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譬如其法译本的出版社瑟伊(Seuil)出版社就是法国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这使得莫言的外译作品能很快进入西方的主流发行渠道,并在西方得到有效的传播。反之,如果莫言的译作全是由国内出版社出版的,恐怕就很难取得目前的成功。近年来,国内出版社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始积极开展与国外出版社的合作,这很值得肯定。
最后,作品本身的可译性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这里的可译性不是指作品翻译时的难易程度,而是指作品翻译成外文后是否比较容易保留原作的风格,原作的“滋味”,容易被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譬如有的作品以独特的语言风格见长,其“土得掉渣”的语言让中国读者印象深刻并颇为欣赏,但经过翻译后,它的“土味”荡然无存,也就不易在非中文语境中获得同样的接受效果。有人对贾平凹的作品很少被翻译到西方,甚至几乎不被关注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贾平凹的作品也很优秀,似乎并不比莫言的差,为什么他的作品没能获得像莫言作品一样的成功呢?这其中当然有多种原因,作品本身的可译性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莫言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既接近西方社会的文学标准,又符合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期待”,让西方读者较易接受。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早有先例。譬如白居易、寒山的诗外译就很多,传播也广,相比较而言,李商隐的诗外译和传播就要少,原因就在于前两者的诗浅显、直白,易于译介。《寒山诗》更由于其内容中的“禅意”,在盛行学禅之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孟浩然的诗。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的跨国、跨民族译介与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涉及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更受制于多种因素。国内有些人往往只是从外译中的角度来看待中译外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背离了译介学的规律。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可以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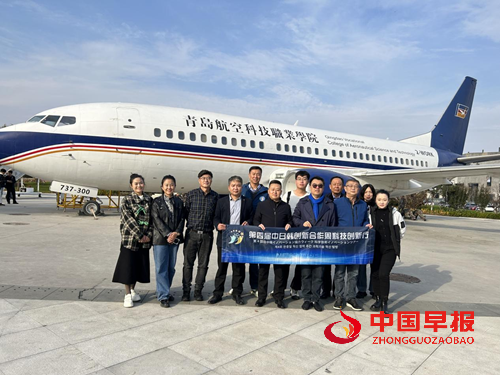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