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亭下茶香聊父事
作者 戴云
父亲住在兴义城区麓山别院小区17栋顶楼,装修时,他特意跟物业申请几次,在楼顶搭起个小亭子。
午后,太阳斜斜地照过来,把木椅晒得暖乎乎的,父亲就端个搪瓷杯,泡上一壶本地的绿茶,坐在亭子里慢慢喝。今年是父亲九十岁大寿,我一有空就陪他喝茶聊天,听他讲这九十年的日子,那些藏在深山里的故事,就像茶香一样,浸人心脾。

父亲戴仲宏母亲胡静麟与儿女合影
1936年中秋节,父亲出生在兴义市敬南镇巴布村石板槽组。那地方全是石头山,土少得可怜,地里种出的包谷只够填个半饱。家家户户住的都是石头垒的房子,屋顶盖着茅草,一下雨就漏,锅碗瓢盆都得拿出来接水。父亲说,小时候最大的盼头,就是过年能吃上一顿白米饭。
父亲望着远处的山,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慢慢说:新中国成立前夕,大伯是云南罗盘区共产党游击队的,他的同志常来家里落脚,把这里当成了联络点。那时候父亲才十多岁,瘦得像根刚冒芽的竹子,裤腿短了一截,露着细脚踝,却已经懂了“翻身”就是让老百姓能吃饱饭、不受欺负。每到夜里,他就揣着个旧手电筒,蹲在村口的山坡上站岗放哨。山坡上全是野草,露水把裤脚打湿了,风一吹凉飕飕的,他却一点不敢动,死死盯着周边的山路、树林,连萤火虫飞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总说,那会儿眼睛尖得很。什么从眼前过都看得清清楚楚。
1959年父亲戴仲宏母亲胡静麟在望谟县王母河畔大桥留影
父亲十五岁那年,游击团的同志让他带路去剿匪。他攥着一根比自己还高的梭镖,木柄被手汗浸得发亮,领着队伍在山林里穿行。山里的雾浓得很,五步开外就看不清人,露水顺着树叶滴在脖子里,他却一点不觉得冷,只记得耳边的风声、队伍的脚步声,还有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没过多久,他还在村里组织起了儿童团,当了团长。清匪的时候,就跟着一起在村口巡逻,手里拿着梭镖,腰杆挺得笔直。等匪患平息了,部队首长特意奖了他一头黑山羊和一床棉被。山羊的毛摸起来软软的,跟着他后面“咩咩”叫;棉被是新弹的,裹在身上暖烘烘的,还带着新棉的香气。父亲说,那是他这辈子收到过最贵重的奖励,晚上抱着棉被睡觉,都舍不得翻身。
1954年戴仲宏(右)在贵州省委党校学习期间与戴显尧(左、省石油公司工作)、戴侗(中,贵阳市公安局工作)于贵阳合影
1951年夏天,父亲跟着地方政府的同志去了兴仁专区行政干校学习。那时他十六岁,第一次离开家,背着个旧布包,包里装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和一双奶奶新做的布鞋,走在满是尘土的路上。太阳晒得他脖子脱皮,渴了就到路边沟里捧水喝,却一点不觉得苦,心里全是对学习的盼头——他想识字,想懂更多道理,想帮老百姓做更多事。在学校里,他学得认真,笔记记得工工整整,老师提问他总是第一个举手,第一批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胸前的团徽擦得亮亮的,每天睡觉前都要摸一摸,生怕弄脏了。结业后,他和三十多个同学一起,从兴仁步行去关岭县城,整整走了六天。白天顶着太阳赶路,鞋底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继续走;晚上就住在老乡家的柴房里,铺着稻草睡觉,醒来身上还沾着草屑和柴禾叶,却睡得特别香。在关岭搞了一段时间的土改,又被调到望谟县新屯村搞土改。村里的土坯房里,煤油灯的光昏昏暗暗的,他和村民们围坐在地上,一笔一笔算着土地账。大家都盼着能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土改结束后,他被提拔望谟团县委当少先部部长,常去学校里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看着一群孩子戴着红领巾,齐刷刷地给他敬礼,声音脆生生地喊:“叔叔好!”就觉得浑身都有劲儿,连走路都想蹦起来。

1954年戴仲宏(右一)在贵州省委党校学习期间与家人和同事于贵阳合影,戴显尧(后左、省石油公司工作),戴仲龙(前左.在省合干校学习),戴仲科(后右.随部队在贵阳驻军)
二十岁那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天特别蓝,没有一丝云彩,他站在党旗前宣誓,手心里全是汗,声音却特别洪亮,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后来他被任命为望谟县委组织部科长,每天抱着厚厚的文件在办公室里忙到深夜。那会儿机关里的煤油灯总亮到后半夜,他趴在木桌上写材料,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成了夜里最常听见的声音。有时候写得太晚,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天亮了接着干。除了审干、肃反这些工作,他还常往农村跑,组织大家搞互助合作社。春天播种的时候,他跟着农民一起在田里插秧,泥巴糊满了裤腿,连膝盖都沾满了,弯着腰插一天,直起来的时候腰都僵了;秋天收粮的时候,他又帮着挑谷穗,扁担压在肩膀上,磨得通红,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却还是笑着说:“多挑一点,老百姓就能多收一点。”他总说,农民的日子不容易,面朝黄土背朝天,能多帮一点是一点,不能让老百姓寒了心。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成了最金贵的东西。父亲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一顿只能喝上一碗稀粥,碗底都能照见人。大家就想办法凑粮食,把包谷胡、包谷壳泡软了,放在石磨上磨成粉,掺在少量的粮食里做饼子。饼子吃起来剌喉咙,咽下去的时候得喝口水才能顺下去,却能顶饿。有时候饿极了,就挖地里的野菜煮着吃,味道涩得很,也得硬着头皮咽。好多人都水肿了,腿一按一个坑,父亲也不例外,他就用麦麸煮水喝,说是能消肿。那时候父亲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眼窝深深的,特别憔悴,却从没抱怨过一句,还是每天早早地去上班,晚上带着一身疲惫回家。母亲常说,那时候家里的粮缸总见底,父亲却总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偷偷往孩子们的碗里多舀一勺粥,自己却啃着包谷壳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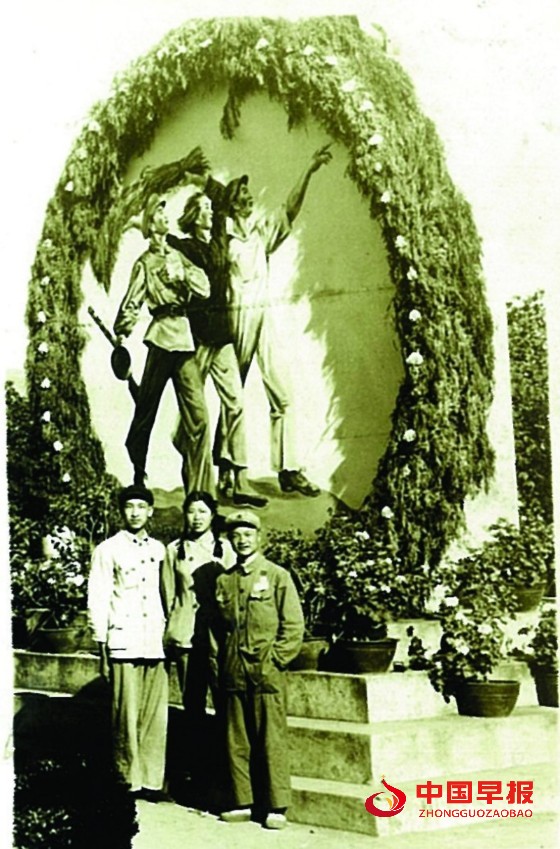
1954年戴仲宏(右)与家人戴显尧(中、省石油公司工作),戴仲科(右.贵阳驻军)于贵阳河滨公园合影
母亲是1954年从贵工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后来分配到贵州省计委工作。1957年,响应“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去了望谟基层。就是在那儿,她和父亲相识了。父亲知道母亲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怕她期满后回了贵阳,基层少了个得力的人,就专门找组织汇报:“望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想留她下来一起干”。组织考虑后同意了,就这样,母亲在望谟一待就是十八年,直到1975年才调到兴义地区计委。那些年,父母和许多干部一样,把家安在了基层,把心也扎在基层。家里的桌子是捡来的旧木桌,修修补补用了好多年;孩子的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补丁摞着补丁,却从没觉得苦,因为心里装着老百姓,装着干事的劲头。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父亲当了财税局的主要领导。那时候我常去他单位玩,单位是个旧院子,门口有棵大梧桐树,夏天满院子都是树荫。赶上他们学习,我就凑在旁边听,搬个小板凳坐在角落,手里拿着个小本子,认真记笔记。大家围着一张长桌,读着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声音忽高忽低,窗外的梧桐树叶子簌簌地落,一片一片飘在地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纸上,晃得人眼睛都亮晃晃的。家里还订了《参考消息》,每期都用一个旧报刊架摆得整整齐齐,报刊架是父亲自己做的,用铁丝拧的架子,刷了层蓝漆。我小时候就是靠着读这些报纸,知道了“新华社”“塔斯社”,还记住了里根、卡特这些美国的总统的名字,有时候还拿着报纸跟父亲提问,父亲总是耐心地跟我讲。
2016年10月在河南商丘“三陵台”参加世界戴氏根亲文化丙申年祭祖大典,与总会理事长戴锦文先生合影
那时家家都是烧柴火。每天放学后,父亲就叫我就跟着小伙伴上山砍柴。冬天砍完柴回到家,就急忙围着火炉子烤手。到了夏秋季节,天热得厉害,河里的水却凉丝丝的,我就和伙伴们跳到河里游泳,打水仗,玩得浑身是水。饿了就回家用开水泡白饭,就着一点咸菜——咸菜是母亲腌的,咸得很,却能下饭,一碗泡饭呼噜呼噜就能吃完。父亲鼓励我空闲的时候,割马草卖,他给我买了一把镰刀、一个竹筐。我背起竹筐,拿起镰刀,在田埂上割一下午,竹筐就满了。一斤一分钱,一下午也能挣一角多钱。城里搞建设,需要大量砂子,父亲就叫我去王母河边淘沙,光着脚踩在沙子里,一铲一铲地把沙子装进袋子里,扛到建设工地,一立方沙能卖一块钱,傍晚回家时,肩膀都压红了。父亲给我递来一碗盐水,他说喝下,体力恢复得快。母亲在一旁说:“太苦了,还是不去了吧?”
父亲却说:“只有劳动才能磨炼人。”
我偶尔还会捡些废铜烂铁,比如旧钉子、破铁锅,送到回收站,一斤能卖一角四。还有排队买米的日子,粮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队,大家手里拿着粮本和钱,聊着天等着。每次买三十斤米,付四块一毛一分钱,然后扛着米袋徒步回家,米袋勒得肩膀生疼,却也不敢松手,生怕米洒了。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也正是这些日子,让我早早地懂得了吃苦耐劳的道理,知道了日子是靠双手干出来的。
2018年在贵阳戴显尧(中)老人家中合影
1975年,父亲调到兴义地区物资局,先是在计划科,后来又去了办公室。那时候他的工作特别忙,经常加班到深夜。我还记得,有好几次我半夜醒来,迷迷糊糊地看见书房的灯还亮着,窗户上印着他伏案工作的影子,头时不时抬起来揉一揉眼睛,然后又低下头接着写。他总说,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老百姓信任我,我就不能糊弄,再累也得把事情做好。也正因如此,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状贴满了家里的一面墙,1989年还被授予“中级经济师”的职称,拿到证书那天,他特意把证书摆在桌上,看了又看,笑着跟我说:“你看,只要好好干,总能有收获。”
1987年的时候,“西南物资商业报社”还聘他当了记者,他写的稿子,没什么华丽的辞藻,全是老百姓的话,写的都是基层的事、老百姓的事,让人读着心里踏实。
2016年在贵阳参加联谊会与邓小平特型演员卢奇合影
父亲在物资局工作那几年,我上初中,放学的时候常能碰到搬运货物的活,父亲就叫我去锻炼。有时候是一车五吨重的水泥,袋子沉得很,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咬着牙把水泥袋从车上卸下来,再搬到仓库里。水泥灰扬得满脸都是,鼻子里、嘴巴里全是,呛得人直咳嗽,累得满头大汗,胳膊也酸得抬不起来。但拿到那几块钱的搬运费时,心里还是特别高兴,把钱小心翼翼地装在口袋里,回家交给母亲。父亲总说,劳动不丢人,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比什么都强,花着也踏实。也正是那段经历,让我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直到现在,也总想着多干点活,闲不住。
父亲在望谟县委和黔西南州物资局工作的几十年里,写了上百份工作报告、总结和文件。他写材料的时候,总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门上挂个“正在工作”的小牌子,不让我们打扰。桌上摆着厚厚的资料,铅笔、钢笔摆了一排,手里的笔写写停停,有时候想不出合适的词,就对着窗户发呆,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直到有了思路,才又低下头奋笔疾书,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特别响。他写的“邮亭党支部的领导经验”和“望谟县养护段开展相关工作的经验”,还被黔西南州委和黔南州委领导批示转发。有一次我翻到那些文件,纸都发黄了,上面还有好多人的批注,写着“经验实在,值得学习”。大家都说,看父亲写的材料,心里清楚,因为他写的都是真话、实事,没有一点虚的。
1991年,父亲响应号召,提前退休。可是他没在家里闲着,说“还能动,得再干点事儿”,就回到了望谟县,在新屯镇坝关办起了“180炼锌厂”。那会儿厂子刚起步,条件特别艰苦,厂房是租的旧房子,机器也是二手的,经常出毛病。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厂里,披着件旧外套,盯着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机器坏了,就和工人一起修,满手都是油污;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啃个馒头对付一下。后来,他又开了个种植场,种包谷粮种,还发展甘蔗种植。春天的时候,种植场里的包谷冒出了嫩芽,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像波浪似的,看着特别喜人;到了秋天,甘蔗成熟了,又粗又长,叶子绿油油的,咬一口,甜水顺着嘴角流下来,甜到心里。父亲说,能为望谟的经济发展出点力,看着老百姓能多挣点钱,心里比啥都高兴。就这么忙忙碌碌,一直到七十多岁,身体实在扛不住了,他才回到兴义的家里。
戴仲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书法为仲宏二哥补壁
如今,父亲已经九十岁了,身体不如从前,走路得拄着拐杖,步子也慢了,但每天还是会准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有时候看到国家又有了新政策,比如农民种地有补贴、看病能报销,他就会跟我们念叨,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比他年轻时强太多了,要懂得珍惜。前不久,父亲生了场病,住了院,医生说病情不太乐观,我们都瞒着他,怕他担心,可他自己却看得开,还是乐呵呵的,跟我们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辈子活得值得了,没什么遗憾的。”他还早早地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亲手写了灵堂挽联:“为国为民熬心几许苦辣酸甜皆尝尽;克勤克俭献余热赤诚坦荡注清风”,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都透着认真;他叮嘱我们几姊妹:“以后百年归天后,要头戴国帽,穿国家标准的干部服中山装,要体现出中国人的气质和尊严,不能含糊。”
看着父亲坐在顶楼的亭子里,晒着太阳,手里握着温热的搪瓷杯,杯沿都有些磨损了,偶尔抬头看看远处的群山,眼神里满是平和。我的心里满是感慨,鼻子也酸酸的。父亲走过的九十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些平常日子,可他在平凡的日子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把每一件简单的事都做好了,把每一段平凡的路都走踏实了。他的故事,就像杯里的茶,初尝清苦,细品却有回甘,滋养了我们。往后的日子,我会常陪他坐在这亭子里,晒晒太阳,听听他讲过去的时光,也跟他说现在的生活——说石板槽修了水泥路,说孩子们都能上好学,说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会带着他的期望继续努力,不辜负他的教诲,也不辜负这美好的时光。

作者:戴云
戴云:中国文化信息协会期刊信息专业委员会专家
贵州省演讲研究会副会长
贵州省康养产业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作家联盟文学指导(作协会员)
历任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副会长
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经管专业教师
中共黔西南州委政策研究室副调研员
贵州省黔西南州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
公开发表文稿400多篇,个人作品《盘江潮影》《盘江潮雪》《探素决策之路》;主编《演说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历史性跨越》《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研究》等作品。
责任编辑:张兆伟
值班总编:邱 天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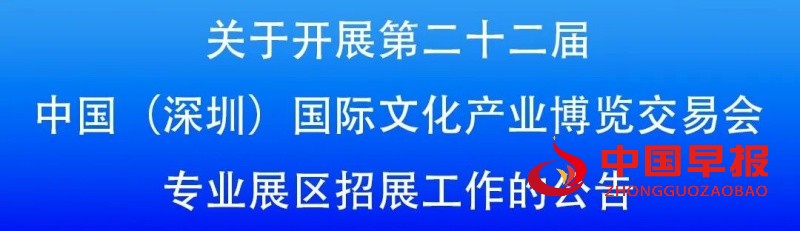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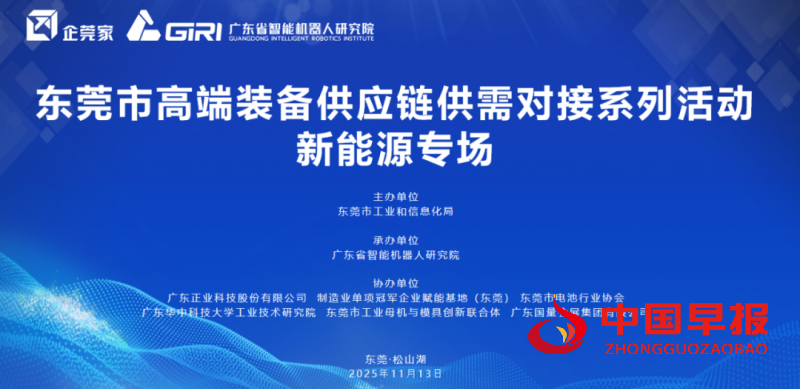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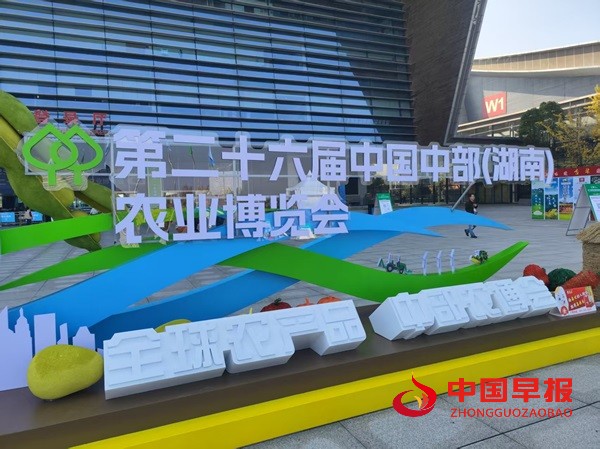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