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董邦耀《 当年我是“火头军” 》
当年我是“火头军”
文/ 董邦耀

每当三线战友亲切地叫我“邦师”时,就会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当“火头军”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二十 五年前,我和八百里秦川二万五千多名十六七岁的初中毕业生一道,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怀着一腔热血和青春,奔赴巴山汉水,与铁道兵、民兵一起,修筑三线襄渝铁路。当时,我不太会做大锅饭,是火热的三线生活教会了我做饭,也教会了我做人。
刚上三线头一天,我就被分配到学兵15连当炊事员。记得做头一顿饭时,手握笨重的大菜刀,面对能烫猪的三口大锅,望着乒乓球桌似的大案板,一群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心里犯了难,二百多号人的饭咋做?切菜、淘米、烧火、担水……虽然都有临时分工,但只要一处遇到麻烦,大家就一拥而上,竟忘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结果是顾此失彼,忙中出错。十来个人忙乎了大半天还是开不了饭,焖的米饭稀软、夹生,还煳了锅,只好请铁道兵连队的炊事员来救援。

同学们得知我当了“火头军”,说我有福气——肚子不受穷。其实,三线学兵连的“火头军”照样得吃苦出力、流血流汗,刀伤烫伤是家常便饭,甚至有跌入开水锅而身亡的。
冬天,寒冷的西北风卷进芦苇席围成的简易灶房,“火头军”们脚穿永远干不了的湿鞋,踩着水唧唧的地面,手握冰冷的大菜刀,切菜的手冻得就像红萝卜。同学们害怕用刺骨的凉水洗菜、洗笼布,更害怕在灶房外顶着寒风烧火。那马蹄形的回风灶又很难伺候,火难生,生着了烧起来又费事,还得达到每人每顿饭用煤不能超过节煤的要求。炉内烈火熊熊,灶外寒气逼人,这“面迎酷暑,背顶严冬”的差事最苦,但“火头军”们谁也躲不过,每人一周。有次轮我烧火,早上4点半就起了床。那天下着大雪,风又特别大,划了半盒火柴才点燃了一小块牛毛毡。架上被雪打湿的劈柴,小心翼翼地关上火门,却听见“呼”的一声,被炉风吸灭了。越急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点不着火。灶房里揉馍的同学在喊:“加火,该上笼了!”天啊,今天完蛋了,火生不着,进洞接班的同学吃不上饭咋办?我心里急得火直往上蹿,患有关节炎的双膝冻得钻心疼,站也站不住,我咬着牙,用两条腿来回换着站立,灭了又点,点了又灭,沮丧得直掉眼泪。火终于点着了,这才有功夫从炉膛里取出几根燃烧的劈柴,生了一堆火。烘烤一会儿冻疼的双膝,又往炉膛里添添煤,钩钩火。谢天谢地,开饭没有晚点,我没有挨训,罪没有白受,悬着的心才放进肚子里。

夏天,“火头军”们身穿工作服,腰系围裙,脖子上搭条湿毛巾,忍受着热气的蒸腾,两手揉馍,锅前炒菜,上笼下笼,飞刀切菜,汗水模糊了双眼,也顾不上擦一把。开饭时,只能留一个人发下一顿蒸馍的一百多斤面,紧张得难以喘息。开饭晚五分钟,晚点名炊事班就要在全连同学面前挨批评。缺水,成了保证按点开饭的大难题。刚上三线时,我们连队炊事班在罗向崖的半山腰,吃水全靠在汉江里挑,一下暴雨,原来清澈的江水一下变成了黄汤,时不时可以发现在江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尸体。挑上去的水,又没有缸存放,只好往仅有的四只桶里撒些漂白粉或白矾,用擀面杖一搅,随着水的旋转,泥沙慢慢向下沉淀,刚能看见水的本色,就将桶里三分之二的水倒进锅里,剩下的尽是泥沙。后来到了罗家岭,做饭是用橡皮管子引来山沟里的水。几个连队都在山沟架了水管,夏天水就更缺,连队之间难免时常发生一些争水的小插曲。有一次,我用橡皮管子往锅里加水时,突然发现冒出了肥皂泡,就要烧开的半锅水吃不成了。我知道又是出洞的同学们在水沟里洗澡,赶忙从锅里抽出水管,飞身跑上山沟,厉声喝道:“喂,找死啊!你们是在自己的饭锅里洗澡,知道吗?这饭还吃不吃了?”但看到大家满身黑乎乎的灰尘,我又心软了,“请大家等半小时,给锅里放够了水,你们再洗吧。”

白天,“火头军”们不知道太阳早上怎样升起,整天为四班倒的八顿饭(进洞出洞各开一次)而操劳,还要出公差,去几十里路外的团部买粮、油、菜。装卸车时,180斤一麻袋的高梁米背上就走,50斤一袋的包谷面最少扛两袋。我们连队都是关中道去的学兵,爱吃面,却一直未吃过压面条。当得知离我们连队二三十里远的一家农户有台压面机时,炊事班长蒋宏亮就派我带了三名施工班的同学去压面。去时抬的是一百多斤的干面粉,几个人换着抬还能坚持,回来时抬的是压好的湿面,越抬越重,口干肚子饿,真想把箩筐扔到汉江里去。好在来时一人带了一个冷馍,啃几口,又继续走。后来一遇过节,压面就成了我的“专利”。
晚上,“火头军”们不知道太阳怎样落下,当开过下午饭,“火头军”们将剩饭填进肚子,涮完锅,洗完盆,又该为晚上12点进出洞的同学们准备晚餐了。每天夜里1点左右入睡前,都要将闹铃上到凌晨4点,因为早上6点进洞的5点半开饭,紧接着换出洞的同学又该吃饭了。“火头军”们紧张得常常连滚带爬。一天夜里下大雨,该做饭了,水管里偏偏没水。我握着手电筒,冒雨爬上山沟去检查。水管依山势隐在草丛中,鬼知道是哪一段出了毛病?当我接好被雨水冲断的水管下山时,脚下一滑,跌入沟中。恐慌中,我的手抓住一棵树根,借助草根、树枝爬了上来,幸好还没摔伤。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大风无情地掀起屋顶上的苇席和牛毛毡,“火头军”们赶紧抽出自己地铺下的塑料单,盖住面粉和大米,再爬上屋顶,用几根绳子绑上重石,分别吊在屋顶压住席子和牛毛毡,才没有让炊事班“开天窗”。就这样,饭还是要准时开的。几个月后迁往新工地时,地铺下面的麦草已腐烂发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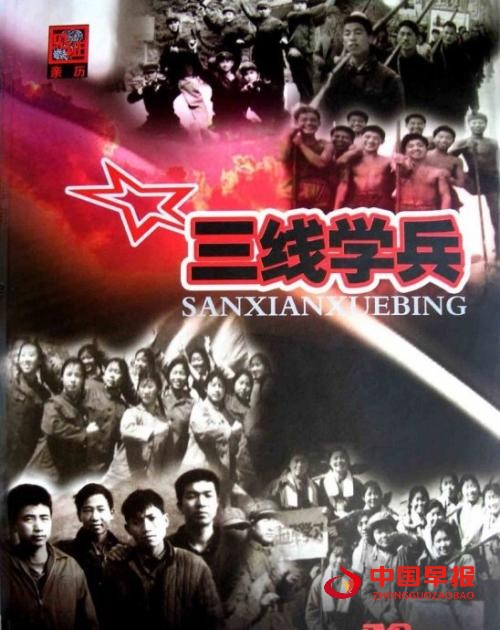
时间一长,我们学会了连刀切菜、蒸馍用碱、炒菜、焖米饭,蒸的馍在几十里的施工线上都出了名,附近铁道兵连队和学兵连的都拿米饭来换馍吃,可惜每顿一人只有一个;而且面也擀得好,一说病号饭是面,“病号”就会陡增,连女学兵连的司务长都夸我们比姑娘们的手艺高。那时学兵们干的是打眼放炮,出渣进料的强体力活,国家给的是每月15元伙食费,56斤的定量,但40%是杂粮,又很少有蔬菜、副食补充,整天是脱水压缩菜、黄豆煮海带、咸菜就米饭,根本吃不饱,能吃上豆腐烧白菜就算过年了。鱼、肉、禽、蛋就更罕见,两瓶肉罐头放在大锅菜里,谁能吃到肉末就很有口福了,肚里哪有油水。有的学兵饿极了拔起地里的豌豆苗就往嘴里送,误把漆树芽当香椿芽吃,甚至有把桐油当香油喝而中毒的。司务长和“火头军”们看到这些心里直难受,却又无能为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厨艺再好,天天熬的高粱米稀饭仍然是一锅红汤,做的未除皮的苞谷糁稀饭难以下咽,同学们一看见这些就皱眉头。为此,我们又学会了粗粮细做,变着法儿改善伙食,用麦面和玉米面做金银卷,用苞谷面蒸发糕,用菜刀削面、磨豆腐、腌咸菜、做豆腐乳、养猪,还在汉江边的沙滩上生过豆芽。
现在,每当家宴上亲朋好友夸我做的饭菜可口时,我就会高兴地说:“我是学兵连的‘火头军’。”是的,我为参加过三线建设而骄傲,我为是学兵群体中的一员而自豪。我感谢三线那段艰苦的岁月铸就了我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庆幸昔日火热的学兵生活培育了我坚毅、刚直的性格。这些收获,将使我受益终生。
(发表于1996年8月13日《宝鸡日报》“峥嵘岁月”征文,收入《春春无悔》一书,1998年与《西安晚报》“三线学兵连”征文《我心依旧》(收入《魂系襄渝线》一书)同获陕西省作家协会、省文学创作研究会第二届“拓荒”文学奖)
作者简介:

董邦耀,笔名骊山、高言,原为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主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1977年以来,文学作品和征文等获奖百余次,出版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大道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个人文集《浅海掬浪》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报告文学集《大道撷英》(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散文集《浪花如雪》(沈阳出版社),主编出版报告文学集、画册《龙脉天路》、《情铸生命线》等,2006年入选《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
相关推荐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