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怀仁瓦盆
王翠芳
童年时,第一次以自己的名义走出村庄是去邻村的小学参加考试,每个小孩子都会警觉地识别出邻座是另一个村的学生。那时,村庄的名字就是我幼小心灵中一个温暖的归属。成年后,走出县区参加工作,单位的同事、领导总会先问你老家是哪里的,我便会用十分谦和的语气说:我是怀仁的。
对方总是很热情地回我一句:哦,怀仁的,好地方。上一点年纪的还会再加一句:怀仁,瓦盆呀!开始听这句话有点奇怪,前半句夸怀仁是个好地方一下子鼓足了我身为怀仁人的骄傲,后半句的瓦盆却说得我一头雾水,难道怀仁是以瓦盆出名的?后来慢慢听多了,才知道的确是因为怀仁多年以来一直出产优质瓦盆,并源源不断地销往周边各个县区以及内蒙古,从而让“怀仁”与“瓦盆”一起在晋北地区人们的口中赢得了美誉,也是所有走出怀仁的儿女们身上一枚醒目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印记。其实,每每别人说怀仁、瓦盆的时候我往往是无言以对。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红色的瓦盆是怎样加工而成的,估计是像家乡的粘土砖一样,经过和泥、成胚、晾晒、烧制而成,好在瓦盆曾经是我童年中熟悉的家庭用具,熟稔的如我的乡亲……

记忆中奶奶的瓦盆小巧而光滑,是用来和面、蒸糕的“糕盆”,糕盆由于用的年久由淡红色变成了绛红色。每天中午,奶奶和家乡的大部分主妇一样,用碗盛好糕面,开始加工中午的主食。每当金黄软糯的黄糕躺在大小适中的糕盆里,奶奶总会倒点麻油抹在热糕上。细密而晶亮的油泡泡遍布糕面,黄糕独有的劲道,加上麻油质朴的香气,仿佛一下子驱散了胃中的饥饿和身体的疲累……
“瓦盆”的概念在他乡被重新唤醒,总是想起它们一只摞一只被粗壮的草绳捆着,一捆一捆摞在铺着干草的马车上。干了的庄稼杆像母亲护佑孩子那般,小心翼翼地护佑着每一个瓦盆,目送每一个瓦盆在往后的日子里各自成就自己。一色均匀的浅红带着泥土的羞涩,被一双双同样母性的手迎进小院,迎上热炕……依稀记得奶奶“开盆”的仪式,奶奶把新买回来的瓦盆先倒满热水,说这是“生盆”。估计是让清澈的水一点点渗透干涩的瓦盆,吸饱水分后增加盆身的韧性,增加瓦盆的使用寿命。生好的瓦盆又被奶奶拎到院子里太阳下,开始下一个“磨盆”的程序。奶奶找来一把干谷子叶,谷子叶干燥而充满韧性,在没有钢丝球的年代那就是最好的清洁用具。奶奶把它醮上水开始打磨瓦盆。当均匀而细腻的力道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地一遍遍走过瓦盆,曾经粗糙略带棱角的莽夫般的瓦盆经过这样的打磨之后,旧貌换新颜。再把光洁绵滑的瓦盆用布头醮上胡麻油底,均匀地涂擦一遍又一遍,最后经过这样一道“上油”的工序。油红瓦亮的瓦盆就像一个刚进门的娇羞的新媳妇儿,不仅光彩照人而且浑身充满了烟火气,这样的器皿就成了可以参与家庭中一日三餐加工饭菜的“熟盆”了。“熟盆”往往会成为主妇们十分珍视的常用家具,经过不断磨合会越用越顺手,在家庭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一些大的瓦盆如斗盆、五升盆之类的一般不会有“上胡麻油”的待遇,至多用蓖麻油细致擦拭后,等办红白喜事才正式上场,这样的大盆子也经常会被邻家借去“办事业”。所以这样的盆子盆身常常带有用红油漆写的姓氏或画的符号,作为某个家庭特有的辨识标记,便于邻里间相互借与还。

想起瓦盆,也总是想起逝去的母亲……那年暑假,长大的我在母亲一遍又一遍的指导下,很荣幸地学会了蒸糕。虽然蒸出的糕至今都无法像母亲蒸出来的糕那样软糯劲道,毕竟是学会了晋北女人必备的持家本领,于是心里美滋滋地体会着一个女孩子长大的骄傲。每天上午还没等下地干活的父母回来,我就早早地生火做饭。把绵黄细腻的糕面倒进母亲的糕盆,一边倒水一边揉搓,认真地蒸糕。等父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时,看到自己拉扯的孩子能做饭了,心情肯定是十分欣慰的。其实那也是我生为人子唯一替母亲分担过的营生。就在那个暑假,有一次我把拌好的糕粉撒进笼屉,在用清水洗盆时,不小心把糕盆掉在地上打烂了。摔碎的糕盆露出醒目的生茬,仿佛就是母亲破碎的心……母亲那次真的发火了。那可是她用了十几年的糕盆,被我打碎的那个糕盆也是我们家最后的一个瓦盆。当时我对母亲的火气十分不屑和不解,认为母亲真落后,一个笨重的瓦盆论轻便光洁不如搪瓷盆,论结实耐用不如铝盆……等我也生为人母,一切日用开销都与孩子挂钩,拿起任何东西都会替孩子着想时,才慢慢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为了把那个家的日子过在别人前面,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她勤勤恳恳在土地上劳作,省吃俭用不乱花一分钱,母亲想把自己的每一份力量都积攒下来留给孩子们……
成家之后,第一次走进婆婆家,看见婆婆的一个瓦盆居然有两道绳疤。细细观察才发现,原来盆身有一道细小的裂痕,由盆沿向盆底方向漫延。我还从来不知道有这种办法可以延长一个瓦盆的生命。婆婆说是她用纳鞋底的锥子慢慢在盆子的裂痕两边对称地打开几个洞,用大针串着浸过油的麻绳缝合起来的。一对洞眼一道线痕,几对线痕紧紧地弥合着盆子的裂口,就这样一个受过伤的瓦盆被挽留住,仍然担负着应有的用途。补好的瓦盆不仅让我佩服婆婆的勤俭与灵巧,更让我看到女性的坚守与坚持!
今天当我用不锈钢盆和面、蒸糕时,才发现这些轻便的盆子不尽如人意。必须一只手按住盆子固定好,另一只手才能去和面或採糕,远不如一个沉重厚实的瓦盆得心应手。但是时代的滚滚潮流早已把当年的瓦盆带走了,留下来的只有绵长的回忆在演绎着那年那月的故事……我生命中的三个女人也都已远去,但她们身上开放过的母爱之花依然灿烂在我的生命里……
祖辈、父辈们曾经沿用着圆底阔边的锥形瓦盆,至今我不知道烧制的师傅不雕不刻是如何把握圆底的尺寸,如何协调阔边的比例,如何做到盆身薄厚匀称、盆口圆润规正、色泽均匀、造型端正,让每一个口径大小不一的瓦盆都能够稳稳当当地用于淘米和面、调菜盛汤而不洒不漏……
温良敦厚的瓦盆渐渐成为一个远去的背影,而刻印在怀仁儿女身上的“瓦盆”印痕已成不朽的口碑,在历史的河流中熠熠生辉!
【作者简介】王翠芳,女,70后,笔名清雅淡卓,山西怀仁人。就职于晋能控股王坪煤电公司。热爱文学,愿以一颗善感的心去体会生活的种种美好。有作品发表在《山西日报》《山西煤炭报》等报刊和网络平台。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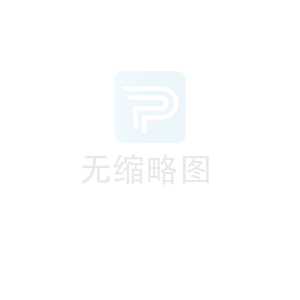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