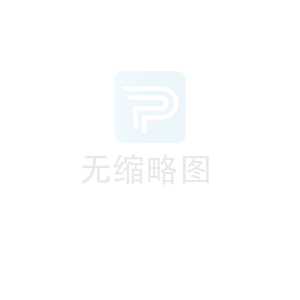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迷人埫随想
摘要:本文通过实地探访神农顶迷人埫,观察阴峪河大峡谷的地质地貌、植被垂直分布及自然景观,结合文史联想与科学解读,展现了该地区深邃险峻的自然特征与生态多样性。作者认为,迷人埫的魅力在于其未被完全认知的原始性与神秘感,体现了自然永恒的奥秘与人类探索精神的呼应。

作者 张文
到神农顶的迷人埫,是在一个雾气初散的清晨。站在观景台的木栏边,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阴峪河大峡谷,仿佛大地突然在此裂开一道伤口,露出它最原始、最狰狞的筋骨。谷深千米,云雾在谷腰缠绕,偶尔散开的缝隙里,能瞥见谷底一线幽暗的绿意——那是至今无人能及的原始森林。
这里的山势是地质年代的史诗。峡谷两侧的岩层如巨书页片片剥露,褶皱与断层记录着亿万年来的地壳运动。阴峪河大峡谷是冰川刨蚀和流水侵蚀共同作用的产物。我想起宋代诗人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这里却是“山裂水隐终无路”,唯有自然的伟力在沉默中宣告着它的不朽。
沿着步道缓缓而行,植被的垂直带谱如一幅渐变的织锦。海拔低处是箭竹林海,竹梢随风起伏,如绿色波涛;再往上是冷杉林,树干笔直如剑,树冠隐入云雾;更高处,杜鹃花丛依偎在冷杉林间。这种层次分明的景观,是山地植被垂直成带性的生动体现。最迷人的是那些依偎在冷杉林间的杜鹃花丛,若在春日,想必是“千丛相面背,万朵百低昂”(仿杜甫《杜鹃》诗),可惜我来的不是花季,只能凭想象去填补那一片绚烂。
步道边的象形石是另一重造化之趣。“石莲花”瓣瓣分明,“惊马石”昂首欲奔,“石熊”匍匐于竹林深处。它们不是人工雕琢的景观,而是亿万年风霜雨雪打磨的杰作。这些巨石,虽无生命,却在岁月的雕琢中拥有了比生命更恒久的姿态。
行至“双龙游峡”观景台,视野豁然开朗。长江与汉江的分水岭在此蜿蜒,云海在脚下翻涌。据说每逢雨后天晴,谷中常现“雾升如瀑”的奇观——雾气从谷底喷薄而上,吞没山脊,人在其中,如坠混沌。这种因峡谷地形与气候相互作用形成的现象,让这里时而明朗如画,时而朦胧如谜。若遇上暴雨初歇,甚至能看到“飞雨上天”的异景,雨滴被谷中强风倒卷,从地面直扑天空。
在“艮震相依”石前,我驻足良久。一块巨岩与一棵古树紧紧相拥,树根如铁钳嵌入石缝,岩体则如盾牌护住树干。这相依为命的姿态,让人想起《诗经》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自然界的共生,或许比人类更懂得何为“不离不弃”。
阴峪河的水声从谷底隐隐传来。这条河在密林中斗折前行,终年不见阳光。它是汉江的支流,虽不如长江汹涌,却以最原始的韧性切割出华中最深的峡谷。河水孕育了大鲵、金雕,也滋养着珙桐、野生枇杷等珍稀植物。
据说这片河谷是白化动物的聚集地,白熊、白麂、白蛇等曾在此出没。它们如同山的精灵,在迷雾中若隐若现,为这片土地披上神秘的面纱。科考队曾在此发现野人的踪迹,虽未得证实,却让迷人埫多了几分未知的吸引力。
回望来时路,步道在竹海中若隐若现。我想起那些扎根于此的守望者——巡线的景管员、科考的科学家。他们与这片山水一样,在寂静中承载着某种使命。唐代诗人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此地有了新的注解:不是避世的逍遥,而是对自然奥秘的直面与探寻。
离去时,天色渐晚。雾又从谷底升起,迷人埫再次隐入苍茫。或许,它的“迷人”从不在于一目了然的美,而在于那深不可测的幽邃,那拒绝被人类完全认知的矜持。正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这求索,或许终其一生,也只能触及其冰山一角。
唯有谷风不息,如天地低语,诉说着永恒的自然之谜。
值班总编辑 邱天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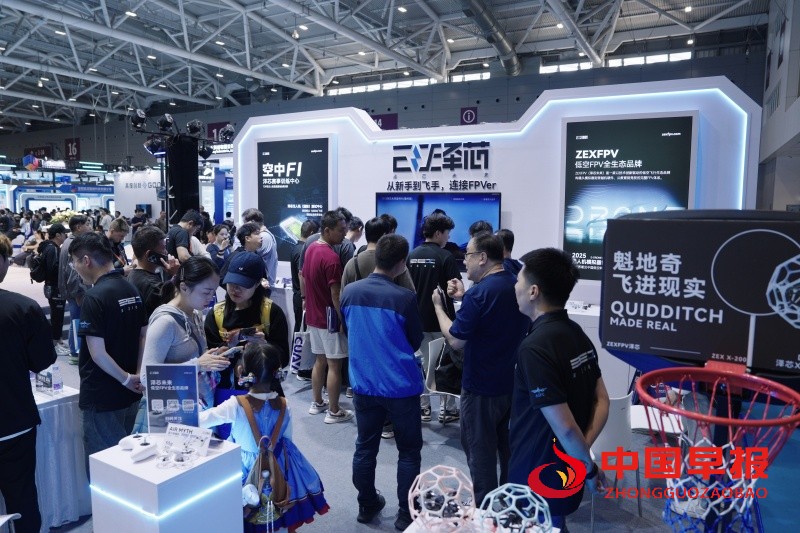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