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新闻


查看手机网站
老家的那棵板栗树
方绍海
到了九月,我牵挂起老家的板栗来。

这是一棵有着五十多年树龄的大板栗树。据六十四岁的大哥说,这是他小时候在野外扯回来的一株板栗苗栽种的。后来,这棵板栗在大哥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二十年后,板栗苗长成碗口粗的大树,大哥也长成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成年的大哥在父亲母亲的张罗下成了家,后来分了家。让我们格外欣喜的是,这棵板栗树不远处的竹林边也有一棵与它一般大小的板栗树。分家时,父母就把这棵树分给我们那个有着父亲母亲和我们另外四个姊妹的大家,那棵由大哥亲手栽种的板栗树就分给大哥的小家。大哥家这棵树在他家靠河的院坝上,与我们那棵树相隔三四米,像是兄弟守望,不离不弃,更像是寓意我们两家本是一家,同宗同祖,血脉相连。

流年无声。我们在慢慢长大,父母在慢慢变老,板栗树在不停地变粗长高。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这两棵板栗树由原来普通的饭碗口粗长到海碗口粗。我家的板栗树高过竹林,大哥家的板栗树枝长叶茂,一边的枝条穿过竹林,与我家的板栗树穿插交互,那种心手相牵、血脉相连的意味更加生动明显。每每看到它们,我就生出一种如见家人的温馨和亲切。每年,我们和大哥家都要打一背篼板栗,打板栗时是我们的欢乐时光。父母在时,我们和父母一起打,一般是父亲擎起一根又长又沉的大竹竿,使劲地敲打树上的板栗。成熟的板栗壳破果绽,砰砰砰砰,不断地掉落,砸在地上,我和母亲以及其他姊妹就忙着在树下捡。后来,父亲去世了,母亲也是五十多岁的年纪了,我就主动接下了父亲打板栗的那根长竹竿。我抬头仰脖,拼尽全力一下一下地敲打板栗,母亲就躬身在树下不停地捡,往背篼里放。我打完了,放下竹竿和母亲一起捡板栗。捡完板栗,我和母亲再用镰刀把少数几个还裹着厚厚青壳的板栗削干净。
虽然板栗都在同一时节成熟,但因为各家安排不一致,往往我们两家打板栗不在同一天。母亲疼爱孙儿,我家如果先打了板栗,她就会让我给大哥家送一提篼,说是给年幼的侄儿。其实我很清楚,这是母亲的托词,她其实也要给大哥大嫂一并送一些板栗,因为那也是自己的后代,亲骨肉、一家人。自然,如果大哥家先打了板栗,他同样也会给我家送一些板栗来,说是给我吃,因为我是五姊妹中的老幺。我何尝不知道,大哥也是要表达对母亲的孝心。

后来,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前几年二哥成了家又分了家,二姐也嫁到了重庆,只有我和大姐分别在老家附近的两所学校当教师。我和大姐都回老家居住,守望着老房子,也继续耕种着老家的田园。板栗成熟的季节,我们和先前一样,我和大姐打了板栗,一定要给大哥和二哥家送一些去。当然,如果大哥家先打了板栗,也要先送给我和大姐以及二哥两家一些。这成了我家的传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同胞手足的温暖。
1995年,我成了家并随工作调动离开了老家,大哥也举家去了县城生活,家里的板栗树就只有靠大姐和二哥照顾了。每当打完板栗,或先或后,大姐和二哥都要给我和大哥两家送过来,或者等我们回老家时再交到我们手里,像是完成了一个具有仪式感的重要交接。

2009年,二哥一家迁到了老家附近的东榆镇,大姐也居住南江县七一中学的学校里安置区,自此,每年打板栗送板栗的任务就成为二哥的专责。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洗礼,两棵板栗树都长成小盆口粗的大树。去年,可能是茂盛的竹林争抢了我家那棵板栗树的阳光和养分,树干朽烂空心了。它像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完成了对子孙后代的最后恩泽。因为没有其他用处,退休后回老家居住的大姐就砍掉了这棵树。现在的老家,只有大哥家那棵板栗树还参天耸立,生机盎然,继续传递着它的温情,延续着它的使命。今年,板栗树结满了板栗。不巧的是,二哥一家去外地打工还没回来;更为不幸的是,大哥四年前中了风,腿脚不灵便,他没法亲自去老家打板栗了。两周前的星期天,我和妻子专程去了一趟老家。看到满树繁硕的板栗在微风中摇曳颤动,不少已经裂壳随时都将掉落,我立即操起竹竿打板栗,妻子和大姐夫在树下忙着捡。打完了板栗,我把它们交到大姐夫手里说:“这些板栗你们和二哥们吃了就是了,这是大哥的意思。”大姐夫感到为难:“那怎么行呢?还是应该给大哥!”“那这样吧,先放你们这里晾干,我们再把大哥接回来,几姊妹一起包板栗抄手,还像小时候那样。”这一次,我擅作了主张。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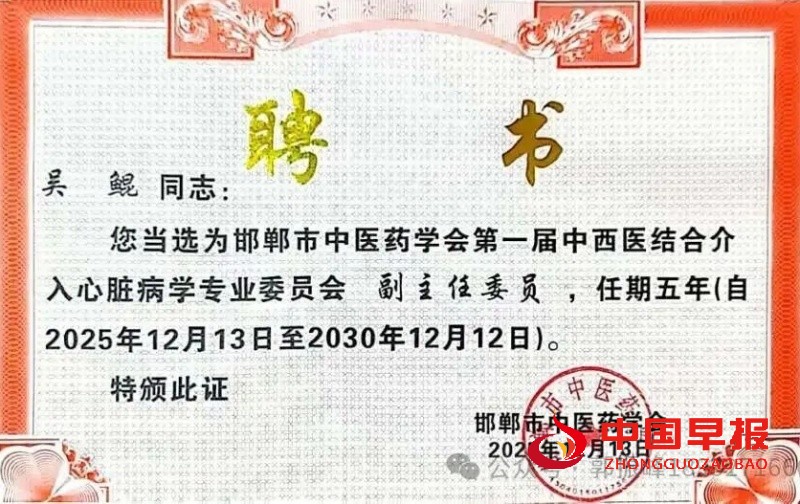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